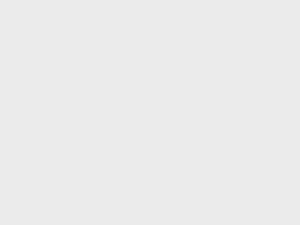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35年,当时在位的周天子襄王之后母弟太叔带勾结狄人争夺王位,襄王被迫出居于郑。晋文公率领军队勤王,杀太叔带,把襄王安置于郑。襄王为了表彰晋文公勤王之功,打算“劳之以地”,即赏赐给他土地。但晋文公对土地不感兴趣,而是提出了“请隧”的要求。在当时,“隧”是天子的丧礼。当天子去世以后,不是直接挖一个坑把棺材放进去就完事了,而是要在都城和墓地之间挖一条长长的隧道,将棺材从隧道中运送到墓地。而一般的诸侯,则是直接在墓地悬棺而下,没有这么一套程序。所以说,只有周天子去世以后,才有资格享受“隧”这样高规格的丧礼仪式,而作为诸侯国君的晋文公,是没有资格的。
现在,晋文公竟然以“有大功于王室”而提出这种大不敬的要求,襄王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严辞拒绝了晋文公。襄王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意思是说,“隧”还是“不隧”不仅仅是拿铁锹、镢头刨地的问题,而是显示了“王”与“诸侯”、“天子”与“国君”的一种差别,是“章显王者异于诸侯也”。现在还没有改朝换代就出现了两个“天子”,恐怕叔父(对晋文公的尊称,古者天子谓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这样的事情也很厌恶吧!如果不是如此,叔父你家的土地多的很,你自己开凿一条“隧”不就完了,何必还来向我请示呢?
果不其然,听完襄王的话,晋文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请“隧”的事情了。
后来,在卫国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
卫国的国君孙恒子曾经在新筑与齐国的军队发生了一次战争,结果卫国的军队打败了,而孙恒子本人也是羊入虎口,岌岌可危。幸亏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名叫于奚的新筑人,出手救了孙恒子。孙恒子为了答谢这位救命恩人,决定赏赐给于奚一个邑的土地。可是,于奚辞谢不受,而是提出要孙恒子马匹上佩戴的繁缨。而在当时,这种繁缨是只能由天子和诸侯所用的辂马所佩戴的,其他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结果,孙恒子碍于情面,还是把繁缨赏赐给了于奚。
据说,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不高兴,他说:“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孔子的意思是说,还不如多赏赐给他一些土地呢!像“名”和“器”这样的东西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土地再多,也仅仅是土地而已,上面没有承载身份和名望。但是,一个小小的繁缨,上面凝聚的却是政治的“礼法”,所以比土地要重要得多。
哲学之所以是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是一种形而上的动物。人不仅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中,而且还要给这些事实赋予意义。前者是经验的事实,后者是超越经验的价值。
正因如此,自然的一切一切,无不打上了人的痕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两个故事。对周襄王而言,晋文公立了大功,完全可以通过“劳之以地”的方式进行犒赏。因为“地”是纯粹的物质和财富,上面没有承载任何意义和价值。多给一些,少给一些,不过是量上的差别,而没有质上的不同。但是,“请隧”的要求,周襄王是万万不能答应的。一条“隧道”,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衡量,它仅仅是一条隧道而已。但是,它上面所凝结的“形而上”的东西实在太重大了,那是纲纪伦常阿!所以,周襄王在这里维持和捍卫的其实是天子的尊严。而尊严和价值,永远都不能和土地进行换算。而孙恒子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遭到孔子的批评。
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终究在世界之外。
文德尔班也说,在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事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越经验的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是表象世界、现象世界、理论世界,价值世界则是本体意义世界和实践世界。与这两个世界相适应,存在两种不同的知识,即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这两类知识有着重要区别。
事实知识都是普通的逻辑判断,比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红的”,就只表示花与红之间的关系,其间丝毫不混杂主观因素。与之相反,价值知识则是表示主体对对象的估价和态度。例如,“这朵花是美的”。这就是我对这朵花的估价。这朵花美与不美,不决定于花本身或花与其他对象的关系,而完全决定于“我”的估价。
因此,价值知识根本不受诸如因果规律那样一些支配事实知识的原则的支配,而是决定于主体的情感、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德尔班说:哲学就是关于普遍价值的批判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