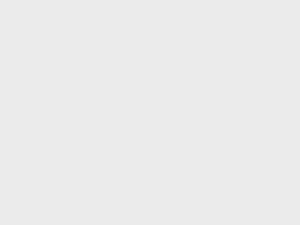很多人初识邓以蛰,是因为他的儿子邓稼先;而更多人熟悉邓以蛰,则是因为他的美学成就,他与朱光潜、宗白华一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邓以蛰的全部著作总计二十五万字左右,与朱光潜和宗白华的几百万字的数量完全无法比拟。著作的数量,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就是这几十倍的数量差距,才显得邓以蛰的美学成就之高,才能说明邓以蛰美学成就的凝练。
“意境”这个词,西方人很难理解,西方美学更难适用,但中国书画艺术的审美最终都归结为“意境”。邓以蛰的美学,就是“意境”的美学。
“书无形自不能成字,无意则不能成为书法。”邓以蛰这句话很直接地说明了形式与意境的关系。形式是中国书画的基础,也是世界书画的基础,在基础这个方面,形式对于东西方书画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书画中,形式却仅是基础,意境才是书画的核心。正如同邓以蛰所说的“无意则不能成为书法”一样,一幅仅具有形式的字,如果缺失了意境那它也只能称为“字”,而无法称为“书法”。同样,一个艺术如果无法具有它自身的意境,那么它也就不能称为“艺术”。
艺术上的“美”可以分为形质之美、虚实之美、性灵之美。形质之美,讲的就是形式的美感。而更深层次的“虚实性灵”则讲的意境的高深。中国的书画,只有达到了虚实之美和性灵之美,才能真正称得上美。换句话说,意境之美可以分为虚实之美和性灵之美。那么意境的“虚实”和“性灵”是如何体现的呢?
“虚实”讲究的是艺术品,尤其是书画中对于整体和谐的强调。整体布局不和谐,不具有美感,那么一个局部再美也是无法掩盖整体瑕疵的。中国的书画艺术,强调的是“以实显虚,以虚显性”。“实”也就是形式必须考虑到“虚”的方面,必须注重整体的美感,才能达到创作者一定的创作目的。在中国,一个作品的创作目的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创作者个人品性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有名的画家、书法家、艺术家,即便不是哲学大家也是品性高洁之人。邓以蛰说“书法以笔画为本,而笔画以筋骨为本”,就是这个意思。笔画是书法的形式,但筋骨架构则是单个字的虚实;单个字又是整篇书法的形式,章法就是整篇书法的虚实;一篇书法是一个艺术家的形式,品性则是这个艺术家的虚实。“字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性灵之美”则是指一个艺术品对于艺术家的品性的反映,这才是一个艺术能达到的最高的美学层次。邓以蛰曾说:“所谓艺术,是性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的境界,非自然中变动不居的现象——无组织,无形状的东西。”一个工艺品,只有加入了创作者自己的性灵——或者说对于现实的艺术化升华,才能达到艺术的层次,成为艺术品。
从“性灵之美”的角度来说,艺术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模仿,不需要鼓励鞭策人类的情感,不能成为功利化的东西,艺术必须要对社会和人生起作用。对于这方面,邓以蛰认为:艺术是用“同情”不断地“净化”人生,要表现高尚的人生理想,而不是满足感官欲望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艺术离不开人生。简单来说,艺术不能完全模仿现实,必须要反映出人类对于现实的迫切需求;但艺术又不能脱离现实,完全脱离现实的话,就无法反映人类对于现实的具体需求。而这互相矛盾的两者之间的抉择,就是对于现实的艺术化加工,这就是艺术家的特质所在。
邓以蛰说:“诗的内容是人生,历史是人生的写照,诗与历史不能分离。”对于社会人生的积极作用,对于历史责任的勇于承担,这才是一个艺术性灵之美的基础——创作者的品性之美。一件艺术品,只有具有了人生的作用以及历史的厚重之后,才能真正体现它积极的一面,才能体现它的意境,体现创作者在美学上的成就。“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者为山水画之开始。”邓以蛰的这段话,就体现了胸具丘壑——创作者的个人品性,对于创作的意境的重要——只有胸具丘壑才能挥洒自如,才能不拘形式。
作为意境的最高层次——性灵之美,邓以蛰曾说道:“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这里的“气韵”指的就是性灵之美。“性灵之美”则正是通过对于人生的激励和对于历史的承担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的激励,就要求创作者能够体验人生的艰难困苦,世上的是非善恶,要求创作者必须贴近生活,必须观察生活;对于历史的承担,则要求创作者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及社会的迫切需求。而这些,综合起来都需要创作者有自己独特的高洁品质——这也正是中国传统认为的“人如其字,字如其人”。正是中国自古不变的逻辑,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有名的画家、书法家、艺术家,即便不是哲学大家也是品性高洁之人”。
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使人们暂时与自然脱离而“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得到一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这种特殊的力量就是创作者的同情、责任,这个绝对的境界就是创作者高洁的道德意境,而这个心境的圆满则是创作者品性、性灵的完美。